老师的书房|吉云飞:读书是为了乐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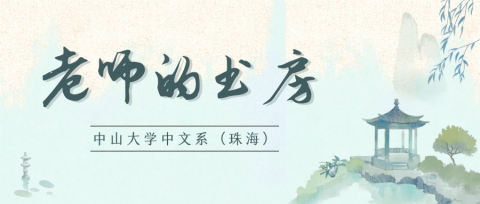
Body
编者按:“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书房,不仅是放置书籍的有限空间,更是理想的燕居之室、读书人的精神角落。置身其中,思绪已然飘至无限的大千世界,思想在此碰撞,灵感在此生发,可贵的精神气质在此熠熠生辉。
本学期,中文系(珠海)将连载“老师的书房”系列文章。本期推送,邀你一起造访吉云飞助理教授的阅读空间,品味书房主人的阅读趣味、审美价值和思想之光。
一、书香也飘书柜外
初进吉云飞办公室,他便很爽快地拉开玻璃柜门向我们展示他的书柜,“随便拍。”书柜上成套的精装书籍摆放齐整、色块统一,看着像书店的典藏本展示区。放在左边柜子最上层的是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布面精装的《汪曾祺全集》,挨着一套砖红色封面的小丛书《我们的经典》,右侧是一套中信出版社的《沈从文别集》。下层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精装的《鲁迅全集》,又横摆着几本塑封未拆的书。右边的柜子则摆了三十多册广州出版社彩图版的《金庸作品集》。谈不上“汗牛充栋”,不过摆着几罐茶叶,几包速溶咖啡,显得生活味还重些。吉云飞端详了片刻,说:“有点乱”,上前整理一番,又说:“哎呀,就这样吧。”
和他对书房摆设的态度一样,吉云飞不是那种太拘小节的人。他随性而为,作为一个“可能已经完全电子化了”的读者,他享受无纸化阅读的便利,突然想看某篇作品,就立刻在手机上搜出来看。他不喜欢“好像买了书就占有了书”的形式上的收藏,除了一些古籍、工具书还有翻阅纸质版的需要,他很少再收藏实体书,以前买过的书基本上也都送人了。他收藏着“一些自己觉得特别值得的书。”遇见投契的作家,就把他们的集子都找来看,觉得不够,就再去找他们喜欢的作品来看。“相遇的品味是相似的”,他向我们解释道。
二、阅读是追求快感的活动
对吉云飞来说,阅读从来都是一个充满快感的活动。他自述“不看没有快感的书”,说自己对“细节特别敏感”,同时性格里又“有很不耐烦的一面。”对于新书,“我没办法地变得有点苛刻。”虽然并非以一个“品评”的心态去阅读,而是抱着一个学习或收获快乐与感动的心态来翻开一本新书或点开一篇文章,但吉云飞往往只看第一段,甚至只看前三句,便立刻就做出了判断,“知道它值不值得我看下去。”他觉得第一段是“作者拼尽全力去奉献出来的”,对“以文字为生”的作者要有更高的要求。所以一年里只有几本新书是值得读完的。但他也鼓励我们,“对你们来说,那个判断的标准是不同的,在你们的论文里面找到一两处还可以的地方就行了。我们都是这样慢慢成长的,而且你们是有希望的。”
在四川小镇的租书店里,网络文学陪伴了吉云飞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在珠海公寓的家中,他的枕边书是一本《论语》。他看书很杂,无拘无束,只求“快感”。吉云飞笑称自己同时看富有“高雅趣味和低级趣味”的书,并认为在二者之间,有一个共通的“好”的标准。他用“真实的满足”和“真实的成长”作形容:“你最想看的书、最能给你带来快感的书,对你而言就是一本好书。或许三五年之后,你会看到它的种种问题,而这是必经的、真实的成长。这样一本书同时也值得我们永远感恩。”
他认为读书的要义不在于获取知识。知识以记忆的方式储存在脑海中,但记忆本身并不是永恒的。不断的阅读实践,真正给他留下的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在天长日久中淬炼成“一种品味、一种判断力、一种审美的能力”。随着阅读经验的丰富,他“非常真诚地觉得”《论语》和柏拉图的《会饮》这些最经典的作品能给人带来最强烈的快感,“这些‘烂熟’的书是我愿意天长地久与之相处的,是我所谓的‘学而时习之’,在我的内心最深处时刻与我以最深的方式相联结。”
三、于网文中窥见自我
吉云飞爱看网络小说。初中时,他便开始接触网文实体书,“自看了网文后,就看不了其他书了。”他每天最晚到教室、放学最早离开,下课铃一响,就冲到租书店借书还书。他偶尔也会把书带到学校,由于担心书本被没收,他只利用课间时间偷偷看两眼。租书店的小说印刷粗糙,封面大多花花绿绿,他很久以后才知道,甚至有同学误以为他在浏览不良读物。
与钻研习题、上兴趣班相比,看网文不像是一个十分“务正业”的爱好。可这份对网文的热爱却成了吉云飞在课业上用功的动力。为了抽出更多时间看小说,他将课间时间都用来写作业;为了争取看小说的自由,他必须保持足够优秀的成绩。在旁人看来,他是一个“特别努力”的人,但吉云飞对“努力”却有不一样的定义。在他看来,努力不是压抑本性,不是为了把自己不那么喜欢、不那么愿意做的事做好,而是在要做的事情中寻找乐趣、把乐趣所在的事情做好、做“满”。“努力”只是吉云飞的一个外壳,他的内在充盈着无法被束缚的鲜活与洒脱。
对网文的长情最终引导着吉云飞走向了研究网文的道路,为网文立法、为属于自己的网络文学发声。“研究网文是为了关注自己”,认识和关注自己是件有趣且幸福的事,因此也不需要太多外部的驱动力。在研究的过程中,吉云飞不断产生困惑,不断向自己发问:“我为什么爱看这类,不爱看那一类?这一类里为什么爱这一个,不爱那一个?”时间长一点,他也学会为自己不那么喜爱的流行作品写评论,并思考:“为什么这么多人真诚地喜欢?我又为何始终不能被吸引?”在镜子的折射里,他逐渐窥见那个隐藏的自我。对吉云飞而言,“阅读兴趣”和“研究兴趣”属于同一种乐趣,“属于认识自己的乐趣,更可以成为一种变化气质的契机。”对于吉云飞来说,求知的乐趣不在于知道更多,而体现为将自己的存在方式转变得更丰富和更充盈。
四、永远走在探求价值和内心的路上
谈到自己为何选择中文系作为自己的专业,吉云飞认为选择中充满了偶然。“我模模糊糊地感受到了其中所蕴含的最有价值的东西。”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上,这种模糊的、对价值感的追求让他进入了文学的世界。回首过往,那层萦绕在人生路口的迷雾已然消散,那种模糊的感觉也已然清晰。“我觉得再来一次,我也会做同样的选择。”
追随着这种“吸引自己的感觉”,吉云飞在中文系的平台上,有三次在不同专业间的转向。他视之为一种“自然”的选择,逐渐找到了自己在学习生涯和学术研究中的定位。本科时,因为性情与古代文学和文献研究有着契合之处,他选择了古典文献的研究方向;博士时,对网络文学的喜爱又让他一头钻入了当代文学研究。他以自身敏锐的洞察力,在自身视野的最大范围之内寻找那个“最有价值”的东西。
价值追求和兴趣导向既是吉云飞自身阅读和研究的方法论,也是他对同学们进入文学世界和学术研究的建议。在吉云飞看来,学术研究中,不从自身兴趣出发所能抵达的“好”,只是囿于一般评价体系中的“好”,在真正的“好”面前就不值一提。“人生到最后靠的就是热忱”,因此吉云飞鼓励同学们勇敢试错,用兴趣和热情驱动自我。
但找到并追随自己的心之所向,常常不是一帆风顺。“找到自己热爱的事物,往往需要很多勇气。”吉云飞向我们解释。最好的结果当然是我们所喜爱的事物恰好也是待遇优渥的、父母支持的、社会认可的,但通常的情况不会是这样,从表面上看也可能恰恰相反。吉云飞认为,做大官、赚大钱这类事情在真正的“好”面前并不重要,追求功利也不一定能获得想要的结局。“本质上我认为追随自己的内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才能抵达‘好’,做‘对的事情’也能自然而然地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吉云飞不希望同学们拘泥于某一书单,读书于他,是一场追随自我感觉的享乐。相异的人生境遇和个体心境,无疑都是影响阅读行为的因素。因此,阅读是一个具体的、个性化的行为。书单仅仅反映了个人的阅读偏好和审美,他不希望以个性化的“读书的口味”“败坏同学们的读书兴趣”。采访最后,不同于推荐书单,吉云飞向我们分享了自己最近在读和重读的书。
【最近在读的书】
《启功口述历史》
《吴小如讲杜诗》
《伊利亚特》
